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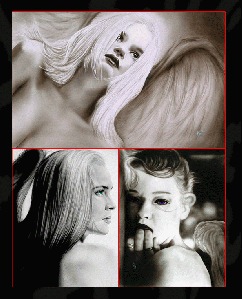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◎活不過九歲
我終於醒過來了。或者這是另一個更深邃的夢境?
門口有窸窸窣窣的聲音,我聽出是我的父母與人低聲交談著。
而我正躺在病床上,虛弱的,甚至抬不起手來,想出聲叫我媽,卻只發得出小貓似的哀鳴。
我不知道我究竟怎麼了,最後的記憶,是我母親背著昏迷中的我,一顛一顛的,在大太陽下趕路。矇矓中我可以感覺到她在哭。
忽然,門口傳來一個較大的聲音,說:「你們最好心裡要有準備,這小孩就算救回來了,也可能有智能上的問題。」
這說的是我嗎?
我閉上眼,又陷入了昏迷。
那一年,農曆是潤七月。
頭一個七月裡,我被一大碗熱騰騰的湯,從腰部以下嚴重灼傷 ─ 那時候家裡正在打牌,我父親突然自牌桌上站起,直接衝到客廳,"轟"一聲倒下,開始抽搐,口吐白沫,大家趕緊圍過來,將他的嘴撬開放進一隻白鐵湯匙,免得他咬到舌頭。卻沒有人注意到一旁跳腳哭泣的我和那一碗我媽媽剛端上桌,卻被我爸爸打翻在我身上的熱湯。
我媽媽回頭罵了我一聲:哭什麼哭?去拿條毛巾來。
我已經痛的說不出話來了,只能哀鳴:燙到了!燙到了!
這時媽媽才發現我的慘狀,火速趕到了信義路新生南路口,林秋江外科。然而褲子已經黏在腿上了,護士小姐只好一點一點的剝下來。
我把頭埋在媽媽懷裡,咬著唇,痛得眼淚直流,卻不敢哭出聲來。
從小我就體弱多病,而且好哭。
但因為好強又比好哭多那麼一點點,所以上小學以後,我很少當人面前哭出來。
尤其是我的父母。
也因為孱弱的身體,我比別的小孩安靜很多,也少有同齡的玩伴,玩伴在一起是要玩的,而我小時候並不怎麼愛玩,只喜歡坐在我父親的大書櫃前,一本一本的,囫圇吞棗。
我一定是利用生病來遠離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和事,雖然那時候我才9歲,根本不明白這個幽暗的心理因素以及後來,這樣子的疏離對我所造成的影響。
當然,現在的我是極度明白,所以我才能那麼武斷地告訴妳,我,一‧定‧是,利用生病來遠‧離‧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和事。
對於一個9 歲的小女孩而言,我的脾氣確實大了點,因為我不喜歡的人和不喜歡的事實在太多了,妳知道的,從小,我就是一個難於取悅的小孩。
我討厭來我們家打牌的每一個大人,偶爾也順便跟著討厭我媽媽,她明明知道我爸爸有癲癇的毛病,不能打牌,偏偏他又愛搶牌打,所以後果總是一樣,打著打著,我父親就忽地狂奔而出,瞎跑一陣後,砰一聲倒下。在我更小的時候,第一次看到父親發病時,我簡直嚇壞了,腦海裡不斷出現的恐懼是「我沒有爸爸了」,「我爸爸要死了」。稍大一點,我會聽我媽媽的話,奮力的在我父親身後追趕,深怕他一個不小心被車撞到或是其他什麼樣不可預估的危險,總之,我一面抹著眼淚一面微弱地喊:爸爸呀 ~~~~ 爸爸呀 ~~~~,然後,眼睜睜看著我的父親在我面前,像棵大樹一樣的轟然倒下。
我幾乎再也沒有想起過這些畫面了。它們依然像當初刺痛著我,我不得不離開電腦前,走到陽台上,朝著對面的淡水河和觀音山,大口大口的吐氣。
好了,就讓我繼續說下去吧。
第一個七月過去了,我復原的狀況出乎意料的好,已經可以跑跑跳跳,爬樹爬牆了。
另一個更大的災難卻悄悄的向我靠近。
那一天是電視上轉播了紅葉少棒在威廉波特比賽的後一天,我家正在大興土木,準備在二樓加蓋一間房,我很興奮,因為那即將是我的房間,第一個我擁有的房間。我正在一個人玩著跳房子 - 隱形的房子,從我們家跳到隔壁楊媽媽家,跳過一條防火巷。
不幸的是,我並沒有跳過去,我直接跳了下去。
根據後來工人的描述,我好像被人推下去的。我一點不記得了。
只有依稀,剪影似的晃動,我被抬了進去,亂成一團,然後是一顛一顛的,我媽媽背著我,一家拒收,第二家也拒收,最後,終於我住進了第三家醫院。
母親說我昏迷了48個小時,唯一醒過來的一次,是一根又粗又長的針,插進我胸腔的時候。
我突然睜開眼喊了聲:痛啊!跟著又迷迷糊糊睡過去。
她說,她就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
我母親很少哭的。她也是好強的不得了,很愛算命,為了算命,她上山下海哪兒都能去。她卻硬說是因為我的關係。
她說我出生以後,她拿著我的八字到處去算,所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一樣的:這個孩子活不過九歲。我腦震盪以後,她抽了個空又去找一個很有名的算命仙,哪知算命仙把八字排了排,嘆了口氣,往旁邊一推,說道:這位太太,妳也不要這樣戲弄我,這個小孩明明已經不在了。
但那些算命的都錯了!我還是活下來了。帶著一種深深的恐懼 ─ 也就是那天在病床上迷迷糊糊聽到醫生所說的「就算救回來了,也可能有智能上的問題。」
所以我一直在等,等自己變成白癡這件事。
以我現在對自己的瞭解,我覺得自己真正的病是孤獨,是想要逃離人群的欲望。
只要是一個人,即使不做什麼我也可以很快樂。
其實一個人可以做的事多著呢!除了窩在我爸爸的書房,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就是圍牆上,大門頂上那一塊小小的屋簷。坐在那兒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我,誰走路是仰著頭走的呢?
彼時流行壁虎功,手腳打開成個大字,兩三下就上牆了。直到前幾年我住在一個眷村裡,也是同樣的矮圍牆,偶爾忘了帶鑰匙,還是高跟鞋一脫,照翻不誤。
啊那時候真喜歡鄭佩佩,不但做著異想天開的俠女夢,還很認真想過上山拜師,偷偷的紮沙包,挖洞練輕功,後來被對門讀初一的男生發現了,著實嘲笑了我一頓,從此我的俠女夢就破碎了。
記得吧?吳興街118 巷25 弄15 號。55 年剛搬去的時候,旁邊還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,還沒有自來水,得走10分鐘路程到附近的一所小學提水,那個小學也就是後來我唸書的地方。
◎ 寂寞的眼神
回頭來看,我真要謝謝自己那段寂寞的童年;它頑強地盤踞在我心裡的某個角落,雖然後來,我看似外向,但我知道它是孤獨巨大的投影。以某一種說法的話。
因為孤獨,我對所有的事情所有人都有了距離,有時候包括對我自己。
也因此,我才有用筆跟自己說話的習慣,文字變成我跟自己溝通的一種基本方式。沒想到這樣的習慣卻遙指我日後的人生方向,當然,這跟我父親有絕對的關係。
父親弄文五十載,著作五百多萬字,跟我,卻無話可說。
常常浮現在我腦海裡的,是父親那寂寞的眼神,那深不可測的寂寞,吞噬了我童年大部份的回憶和快樂,也吞噬了他自己。
但我記得我曾經很愛他的。
那時候他除了編中華日報副刊,還跟馮放民等人辦了一個作品雜誌。在博愛路的三愛大樓。我和弟弟常去那兒玩耍,雜誌社長的什麼樣我老早忘了,但我還記得一樓的咖啡廳,和冰淇淋。約莫父親常去那兒寫稿,總之,那兒的女服務生跟父親挺熟的,笑嘻嘻地逗著我和弟弟,並說:林先生,是您的孫子嗎?好可愛!
於是我就看見父親眼中一閃而過的寂寞,和嘴角上那抹久久不去,極不自然的苦笑。
我把面前的冰淇淋推開,沒法吃了。
這是我對父女之情,僅有的,一個較清晰的記憶了。
一直到去年的十月,關於父親的回憶,才慢慢湧現;如潮汐般,日夜拍打著我的情感,與文字。
父親走以前,孤獨地在武漢近郊的小公寓裡躺了三年。
那時,他的老人癡呆日趨嚴重,家中也正逢遽變。
而我才剛結束我的長期流浪,回到家,面對這些壓力,我表現得很堅強,就像一個長女般。
父親的病並不影響他對我的不滿,自從那個深夜,他把好不容易做好的假牙,又掉進馬桶裡,我責怪他不好好睡覺,整晚走來走去幹嘛。
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,因為他渾身發抖咆哮道:
「妳不要這樣跟我講話,我受不了。」
不久,彷彿跟我鬥氣似的,他摔了一跤,再也沒有下床。
看著他在病床上日益萎縮的軀體,我知道,他正慢慢的離我遠去。
那個夜裡,我聽見他叫『媽媽』的聲音,微弱而持續著,我趕緊推門進去看。
照顧他的看護睡得正熟,父親卻是睜大了眼,右手凌空抓著,抓著。
我握住他的手,問他怎麼了?
他看了我好一會兒,「餓了。」他說。
我替他泡了一碗麥片,放進一塊我從台北帶來的蜂蜜蛋糕,這是他最喜歡的吃法了。
我一匙一匙的餵他,他張著無牙的嘴,一癟一癟,像隻嗷嗷待哺的幼鳥。
吃完了,他突然抓住我的手,放在他的嘴前親了一下,好像看到天使般,燦爛的笑了。
「謝謝妳」。他說。
有記憶以來,父親從未如此坦然的表達他的感情,尤其是對我。
費了好大的勁兒,我忍住呼之欲出的眼淚,強笑道:
「謝什麼啊?我是你的女兒啊!」
「啊?!」父親怔怔地望住我,彷彿我說了件令他迷惑的事。
「我是你的女兒啊!我是岱維啊!」我又重覆了一遍。
「喔!岱維。」
父親輕輕嘆了口氣,渙散的目光落在遠方一個不確定的焦點上,然後,眼睛閉起,發出鼾聲。
坐在他的床沿,我貪戀的看著父親,好想把他搖醒,告訴他,爸爸啊,我已經用盡最大的力氣愛你了,你知不知道啊?
所以,妳能告訴我嗎?為什麼我的體內總是在極端的拉扯,冷淡的熱烈的,記得的不記得的,愛與不愛;兩點間似乎存在著一個更大的陰謀。
而妳,是不是那個不知不覺的共謀者呢?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